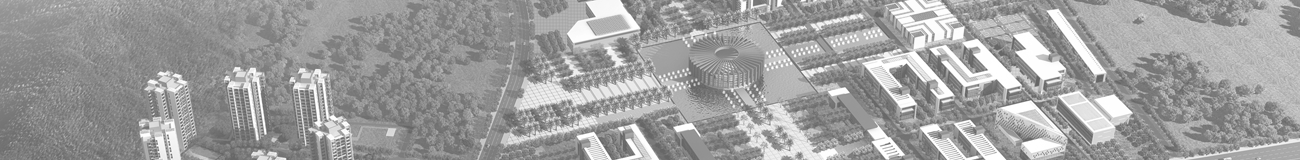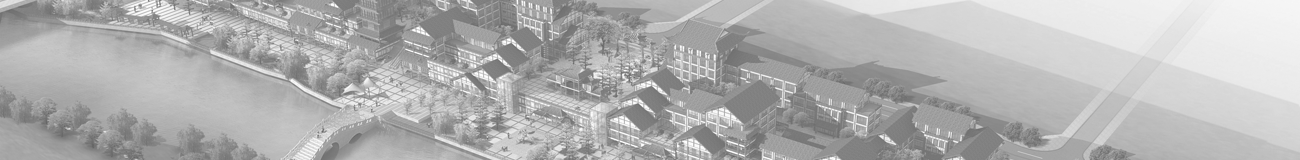景观部 刘佳
云贵高原上千井之城的传说
位于黔桂交界处的独山县,是滇、黔、川通往华南沿海的交通要道,素有贵州“南大门”、“西南门户”之称。独山建制久远,从古到今均是黔桂两地交界的重镇及商城,厚重的人文民俗和得天独厚的自然山水,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独山情韵。

在这座历史悠久的黔南小城里,星罗棋布着或留传自上古,或穿凿于近代的清泉水井,令人惊讶的是,独山的井都有名字,而且每一口井都有一个神奇的传说。正是这些上接日月星辰,下通龙脉水宫的灵性之物,成就了独山“高原千井之城”的美誉。
除了拥有神奇的古井文化之外,独山还是贵州南派花灯的发源地。作为一种雅俗共赏、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,特色鲜明的独山花灯广泛流传于黔南城乡各族。独山花灯产生于“社”的祭祀活动,是一种说白、歌舞相结合,风格独特的戏曲形式,其曲调、舞蹈蕴含着浓郁的地方气息和鲜明的民族特色。
数不清的古井传说
中国西部高原上的千井之城
独山县城位于红水河与都柳江分水岭的突出台地,海拔在970~1000米之间,四周河流均为河源型河流,源短流细,大都分布在800~900米高程,取水比较困难,因此民间自古便流传着“好个独山州,水往四处流”的俗语。好在独山地下水资源十分丰富,掘地三四米或七八米,便有泉水潺潺流出,为供应百姓用水,保证农耕,井,由此应运而生。

起初百姓们只将井打在城内外、街巷中,后来,许多人家为取水方便,便在房前屋后自行打井,更为有趣的是有的人家把井打在自家的地板下面,或橱房里,其方便程度不逊于自来水。时至今日,独山县城内外的古井早已形成星罗棋布之势:各家各户的井,大街小巷的井,就连城外山村里、森林中、田坝里、山路边、古树下都分布着古井。
独山究竟有多少口井?没有人数的清,几乎每家每户、每一个庭院都有井。独山的井不但数量多、水清甜可口,而且形态各异,颇为有趣。有方的、圆的、长方的、两个相连的……独山的井都有名字,十分丰富多彩,如“冒沙井”、“豆芽井”、“锅盖井”、“紫泉井”等,还有不少井名是少数民族语言的译音,此外,独山的每一口井都有动人的神奇传说,充满了奇特的人文民俗色彩。
相传古时候,独山有一口井是海眼,井底孽龙经常通过这里跑到人间为非作歹、伤人害畜,饱受孽龙欺凌的百姓只得向天祈祷,求得观音菩萨惠泽,后来观音菩萨用一口大铁锅把孽龙反扣在井底,孽龙再也不能从这里出来作恶了,从此这口井因此而得名“锅井”;另外一口铜鼓井则有这样一个传说:当年夜郎王带兵路过独山时,兵将们口渴难耐,就掘了一口井,苦于没有盛水器具,就用铜鼓盛水供练武的兵将用,此后每逢月白风清之夜,到铜鼓井来,用耳朵贴着井边去听,就能听见夜郎士兵敲击铜鼓的声音;此外,位于独山县城民族中学内的文庙井,则是因为东汉教育学家尹珍而得名。据传东汉教育家尹珍曾在此结庐开馆教学,尹珍每日煮茶、煮饭汲用的水便是从文庙井中提取的,人们说,喝此井水,人会变聪明。所以,此井又有个俗名:聪明井。
流传于独山民间的古井故事绝不仅于此,除了“锅井”、“铜鼓井”、“文庙井”之外,其它有名的井还有“桂花井”、“沙井”、“擂钵井”、“姊妹井”等。另外,独山还有同时可容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打水的“大井”,也有仅容一只水瓢的“瓢儿井”,这种袖珍型的小井虽然小,但流量却很大,一瓢刚舀起,马上又充盈,一年四季汩汩不息。正因为独山古井众多,井文化丰富,因此独山县城也被誉为“高原千井之城”。
民族融合,多元发展
成就独山“花灯艺术之乡”美誉
独山花灯是流行于独山地区的一种叫“花灯”的民间歌舞和由这种民间歌舞延展而成的一种名为“花灯”的民间戏曲的统称。历史上,独山经历了多次较大规模的民族融合,事实证明,独山花灯形成的历史源流与外来文化的切入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。

清朝时期,为了防止盘根错节的关系网,促进各地区经济文化增长,清政府决定实行流官制,到独山上任的浙江人赵完璧,江西人解韬等都为独山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,客观上促进了独山花灯文化的民族融合。据道光辛丑年(1841年)郑珍、莫友芝纂《遵义府志》风俗卷载《田居蚕室录》:“上元时,乡人以扮灯为乐……,其中所唱十二月采茶歌。如:三月采茶茶叶青、茶叶脚下等莺莺。二月采茶茶花开、借问情侬几时来。音词清婉、莫详所自。”从“莫详所自”中,不难看出采茶调并非本地所出,而“侬”显示了它具有吴歌、西曲的遗声。道光二十二年(1842年)纂修的《松桃厅志》‘风俗志’中:“……元宵有采茶歌、川调楚调不一、各操土音歌咏。”的记载,则表明了采茶歌中蕴藏着川、楚音调。
抗战期间,独山一度出现战时“繁荣” ,连年的战火,造成了独山人口的大量迁移,各地方戏曲文人的流入,给独山花灯带来了丰富的养料。这一时期的独山花灯吸收改良了大量的外来艺术,戏舞结合突出花灯的综合性,使表演逐步程式化,形成用歌舞演故事的“灯夹戏”风格。黔南事变前夕,各地难民涌入独山谋生,使独山人口骤增,促进了汉、苗、水、瑶、布依族等民族聚居地的形成。各民族带来的民俗文化,加速了当地民歌、舞蹈及劳动人民思想、感情、习俗、语言、生产、生活与江西“采茶”、湖南“花鼓”、“花灯”以及湖北、江南小调的融合。
独山花灯的发展,经历了一个由一元到多元的发展过程,即由“地灯”到“愿灯”,再由“愿灯”到“台灯”的演变。地灯不择场地,是一种初期地下跳唱的娱乐形式,其表演形式多为扇帕舞,曲调明快、诙谐,生活气息较浓;愿灯是另一种地灯的表现形式,与普通地灯的区别在于,愿灯主要用于驱鬼辟邪、酬神愿、招财送子等;台灯是地灯与愿灯发展而成的综合性艺术,需要登台表演,因而又称耍灯,其乐曲民歌风味较浓,舞蹈纯净质朴,是花灯艺术与舞蹈的完美融合。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,独山艺人创作并演出了《踩新台》、《打头台》、《七妹与蛇郎》等上百出花灯剧,参加省和国家调演比赛屡获大奖,在海外演出也受到好评。独山县也因此被文化部授予“全国文化先进县”的称号;独山县的基长镇也被文化部授予“中国民间艺术之乡”。